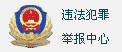○叶碧洒
小时候,一到冬天,“打米呈”就成了村里家家户户的头等大事。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米呈是堪比糖果的年货。家里来了客人,擂上一钵客家擂茶,再配上米呈,便是最体面的招待。各家打米呈的数量,全看家境:拮据些的打一两格普通米呈,宽裕的则能打七八格用料十足的花生芝麻米干呈。
因工序繁杂,米呈都是三四家凑在一起轮流制作。大人们对此格外郑重,甚至要关起门来打米呈,仿佛要守护这香甜的秘密;更不许我们在旁乱说“打松”之类不吉利的话——若是米呈松散不成形,过年可就拿不出像样的年货待客了。
打米呈的日子,几乎像过节般隆重热闹。冬日的阳光刚爬上屋檐,邻里的婶子们便提着自家炒香的米、花生和芝麻陆续赶来。妈妈早已将擦洗干净的正方形“米呈格”和磨得飞快的菜刀摆放整齐,一场“米呈盛宴”即将开场。
厨房里,土灶的火苗正旺,一位婶子添着柴火,妈妈则站在灶台前,用长柄锅铲不停搅拌着锅里由白糖和麦芽糖加水熬成的糖水。清澈的糖水渐渐变得浓稠,冒出细密的泡泡。快熬好时,妈妈用筷子挑起一些糖水,滴进一碗冷水里,接着用手一捏,若能凝成糖块,便说明火候到了。
“好了!”妈妈话音刚落,旁边站着的婶子立刻将妈妈准备好的炒米、花生和芝麻全倒进锅里。妈妈手腕一使劲,铁铲在锅中快速翻拌,金黄的炒米瞬间被亮晶晶的糖稀裹住,浓郁的香气一下子弥漫了整个屋子。拌匀后,妈妈用大木勺将米呈舀进米呈格,另一位婶子早已拿着碾筒严阵以待,双手紧握碾筒两端,麻利而用力地将米呈碾平。她神情专注,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仿佛在雕琢一件珍贵的艺术品。
待米呈在格中压实定型,便轮到菜刀上场。妈妈会依着米呈格边上的格子记号,细心地将米呈切成长方小块。
整个过程,从熬糖到切块,每一步都讲究“快”——怕的是糖水一凉,粘性不足,切时容易松散。这不仅可惜,更被大人们视为晦气。可我们这群孩子,却巴不得米呈松掉——成功的米呈要放进米呈箱(俗称“油箱”)珍藏,只有客人来了才能吃;而松散的米呈,大人们是不会拿来招待客人,平时我们就能大饱口福。
切好的米呈码在簸箕里,像一块块金黄的小砖头。妈妈小心翼翼地将它们叠进油箱,盖好盖子,仿佛在珍藏一件稀世珍宝。随后,大家又马不停蹄地开始准备制作下一家的米呈。直到夕阳西下,各家才提着沉甸甸的米呈箱,心满意足地回家。
那时的米呈,花样虽不比现在,却各有风味。最常见的是白糖普米呈,用粘米炒米和白糖水制成,无花生芝麻,朴实无华,唯有纯粹的甜香。还有黑糖米呈,以黑糖水制作,带着浓郁的焦糖香气。这两种米呈是普通人家常打的。
更“豪华”的是“米干呈”,用糯米炒米,加入花生、芝麻,以白糖水打成。口感丰富,花生的脆、芝麻的醇,让每一口都充满惊喜,吃完齿颊留香,令人回味无穷。这等美味,只有家境较好的人家才打得起。
在那个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米呈是陆河客家人用来招待客人的珍贵食品。吃的时候,通常会配上一碗香气四溢的客家擂茶。一口咸香的擂茶,一口香甜的米呈,那滋味,至今想起来都觉得无比惬意。上了年纪的人,口齿不好,通常会把酥脆的米呈浸进擂茶里泡软一点才送进嘴里吃。
正因为珍贵,米呈平时是不会随便拿出来给孩子吃的。妈妈总是小心翼翼地把那个沉甸甸的米呈箱藏起来,要么放在高高的橱柜顶上,要么就藏到阁楼上面,连梯子也要一并藏起,防止我们偷吃。
如今的米呈,花样早已远超从前——有用鸡汁面做的,有用粉丝炒香做的,还有加入小米、玉米甚至葵花籽的,配料越来越丰富,选择也越来越多。
可任凭它花样再多,在这个物资丰裕的时代,人们似乎不再像从前那样热衷吃米呈了。买来尝一口,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再也吃不出儿时那种纯粹的香甜,也找不回那种“物以稀为贵”的期待与快乐。
儿时米呈的香甜,早已不是单纯的味觉记忆。它裹着乡村邻里的温情,装着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那口香甜,连同妈妈亲切的笑容、那个充满烟火气的小村庄,都成了回不去的过往,化作了我心底最柔软也最沉重的乡愁。






 粤公网安备 44150202000069号
粤公网安备 4415020200006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