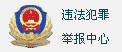○王映婵
“青草池塘处处蛙,黄梅时节家家雨”,窗外雨丝如帘,春已老,那些充满诗情画意的青梅已从树上轻盈地跃下,跳入人间,滚落红尘,在街头安静地等着被哪户人家相中,然后完成它成为食物的最后使命。

腌青梅(网络图片)
每年梅子青时节,母亲就是这样被街上的青梅吸引,一袋一袋买回家里,咸的、甜的,一大玻璃瓶一大玻璃瓶地腌制,然后一个电话一个电话打给出门在外的她的孩子们。
“青梅泡好了,咸的、甜的都有,过来拿。”
这个时候的母亲总是无比自豪,也许每个到了老年还能为子女发挥自身价值的父亲或者母亲都会感到特别骄傲的吧,我想。但是,很多时候,我却并不买母亲的账,“太多,浪费。”我常常这样念叨。
“大出手”是母亲置物的习惯,她买的青梅不是一般人的几斤,最多也不过十来斤,而是几十斤,甚至一百斤。制作甜梅又不容易,工序很多。要把青梅洗净,拍裂,再用大量的盐浸泡过夜,当中要不停地换水;去了酸味的梅子洗净、晾干,下大量的糖,等过一夜或者两夜,再把融化出来的糖水滤掉;最后才一层梅一层糖地封装进玻璃瓶。最气人的是,不知是漏气还是没有充分晾干水分,辛辛苦苦做出来的梅子有时候还会冒泡变质变坏。所以每次看到母亲堆积在家里的酸梅,我就皱眉心烦。我在想,我该如何让母亲知道,丢了几百块钱我不心疼,但看着母亲亲手做出来的梅子就这样浪费了,我会无比心疼,甚至舍不得丢掉而吃下变质的梅子。
我在数落母亲闲得发慌、没事找事的时候,母亲总是像犯了错的孩子,“再也不做了,再也不了。”她低眉轻叹,用一种低得我几乎听不到声音,“其实很辛苦的,那么多梅子,又花了那么多钱。”
可是到了第二年,“青梅如豆柳如眉”,母亲又会数着日子等梅子成熟。没过多久,母亲又一个电话打过来:“过来拿梅子,咸的、甜的都有。”还不忘补充,“你把玻璃瓶里的梅子分装进小瓶子里,然后拿给你的同事朋友们吃,吃了你的梅子,他们受了你的好处,就会对你好——小瓶子我都准备好了。”
母亲的话无比质朴、充满尘俗的处世智慧。但我几乎笑出声来,母亲应该有一颗七窍玲珑心,每一窍都氤氲着为她的孩子化解难处的心思。
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母亲的“大出手”,面对堆积如小山似的青梅,我终于不再有微言。浪费就浪费吧,人越老越需要自我价值的体现,越需要被孩子们“看见”,越需要表达爱与被爱。只要她老人家高兴,又有何不可呢?
如今,腌制青梅的糖水渐成琥珀色,仿佛浸泡了历代诗词意境的梅子,泛着清洌的古典美。而梅子却逐渐发皱,就像母亲的脸,每一道皱折都隐含着深深的爱意。






 粤公网安备 44150202000069号
粤公网安备 4415020200006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