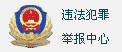●许宇航
在道特淖尔的一个小盆地遇见了敖包会,我一开始还以为是赶集,在一片草地之上集结了很多汽车,往里就是围了一大圈人,停车驻足,原来圈内正有四对人在摔跤。边上的山上挂着风马旗般的彩带招摇,经风猎猎作响,圆锥形的山体就是敖包,神显然已经祭过,主席台上,几个盛装的蒙族老人席地而坐,桌上摆着食物,在他们的身后,扎着三个蒙古包,这样的场面如同海陆丰神诞做大戏时的场面,祭神、放炮头。我们正赶上跤手摇摆跳跃上场展示力量,捉对示范或者热身,之后跤手轮番上阵以力量与技艺进行淘汰,对于一圈的蒙族人来说,我们几个异乡人只是意外的闯入者,这样的信仰盛事,对他们则是固定的一年一度的约定,并借此保留、延续了传统。
初见敖包是在罕山,就在昨天,石头垒成的敖包插着树枝,颠覆了我之前对于它的想像,穹庐的形状倒是有几分蒙古包的模样,但更像是扩大了的玛尼堆。敖包最早是草原牧场石头堆起的边界标志,或者是界石,就如粤东揭西的三山国王,本就是惠州府与潮州府的界石,后来有了香火成神,如同土地伯公,保佑一方平安,又外延传说成了山神,神格节节攀升。敖包当有异曲同工之妙,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加入了诸如长生天、土地、祖先的元素,原始的萨满混合着藏传佛教的仪轨,在平坦的草原,借助孤立的圆锥山体,或者垒石,成了牧人骑行的灯塔,成了神灵栖居的住所,以此铸成蒙族人心灵的高度,每年以约定的时间相聚相会,进行天人合一的沟通。
几天后在奈曼旗的白音他拉苏木,又一次见到敖包会。当地蒙族诗人野岸驱摩托车在前方引领,车穿行在玉米地间的沙土路上,草原已为农田所淹没,良久之后的莽莽田野之中,空出的一块沙地之中垒石的敖包出现,围着四处赶来的蒙族人及车辆,只是不见马匹。祭祀已近尾声,我们随着拥来的人群围着敖包向左绕行三圈,以入乡随俗的姿态融入顺时针缓行的队伍,致敬草原的虔诚。绕行的人群随后散开,在旁边自觉围成一圈举行摔跤比赛,感觉如同一曲田野上的牧歌,在农耕的围剿中每年践约而来依时吹响,透着几分野性,在合围中分享孤独与热烈,在这片曾经的牧场,沙化又复绿的土地,做着游牧最后的挣扎。不知为何,这略显悲壮的一幕,田野版的敖包会,比道特淖尔草原所遇,视觉感觉上的冲击,显得更为强烈,回声久久在心间激荡回放。
再见敖包会,是在三年后的通辽,参加一个大型的文化活动,观光的车队向科尔沁左翼后旗的阿古拉草原疾行,先是大片成熟的稻田在眼际出现,一下改写了我对草原的旧观,随之就是大片的水泊白音查干淖尔湖在车窗外绵绵掠过,掠过的还有丰茂的水草、惊起的水鸭,倒映大湖体态浑圆如笋的双合尔山就在水的尽头出现。目力所及,双合尔山卓尔不群,在这一大片草原中是唯一的山体,如宁夏的西夏王陵,不同的是,同样遗世独立却又以草色与大地融为一体。我隐隐意识到,这就是今天祭敖包大典的崇拜对象,山顶之上有藏传佛教的白塔,这是我所见的最大的敖包,祭拜仪式就在山下铺设的木板之上进行,官方的大典开合进退起伏有度有着演的成分,祭拜的似乎是土地,注重的是礼,有铜制的摇铃声声令我倍感亲切。这让我愈更怀念从前草原、田野所见,还有那辗压青草所散发出来的丝丝缕缕若隐若现的,青涩的气息。






 粤公网安备 44150202000069号
粤公网安备 4415020200006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