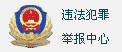○陈莉君
昨夜走过楼下那家新开的客家菜馆,蒸笼里飘出的米酒香。那甜醇的气息,让我在初冬的街头怔怔良久,恍惚又回到了外公的灶间。
初冬的晨雾还未散尽,外公便开始在灶间忙碌起来。新收的糯米在清泉中浸泡了一夜,此刻正散发着淡淡的米香。外婆坐在矮凳上,将浸好的糯米倒入木甑,灶膛里的柴火噼啪作响,蒸汽袅袅升起,模糊了窗棂。待糯米蒸熟,外公便将其摊在竹匾上,待温度降至微温,撒上酒曲细细拌匀,最后装入陶瓮,覆上棉被保温。三日后的黄昏,一缕甜香便会从瓮中悄悄溢出,日渐浓郁。
我总被这香气勾得坐立不安,绕着灶台打转。外婆看出我的心思,轻拍我的脑袋:“阿妹,係酒哦,细人得唔好吃啊。”她越是这样说,我越是好奇得心痒。终于等到一个午后,趁大人们都在田间,我搬来小木凳,踮起脚尖,颤巍巍地揭开陶瓮。甜醇的酒香扑面而来,我用勺子轻轻一舀,连酒带糟送入口中。初时只觉得甜滋滋的,便贪心地一勺接一勺,直到晕晕然,竟趴在灶台边沉沉睡去。醒来时已是夕阳西斜,外婆又好气又好笑地看着我,那目光里的温柔,比米酒还要醉人。
当山野披上新绿,春的盛宴便拉开了帷幕。我们这些孩子揣着粗布缝的小布袋,呼朋引伴往山里钻。紫黑色的山捻子藏在墨绿叶间,熟透的果实饱满发亮,轻轻一碰就落入手心。咬破薄薄的果皮,清甜的汁水瞬间盈满口腔,那股独特的蜜香久久萦绕在齿间。下山时,我们总不忘在向阳的山坡寻觅蕨菜。春雨过后,这些顶着螺旋嫩芽的精灵从腐叶间探出头来,紫褐色的茸毛在阳光下泛着细碎的光。
最妙的要数舅妈烹制蕨菜的手艺。她坐在井台边,掐去蕨菜的嫩尖,用新汲的山泉水反复淘洗。灶膛里的柴火燃得正旺,大铁锅烧得发白。一勺新熬的猪油滑入锅底,瞬间化作澄澈的油泉。拍碎的蒜蓉跳进热油,“刺啦”一声炸开满屋香气。焯过水的蕨菜倒入锅中,锅铲翻飞间,翡翠般的色泽愈发鲜亮。那盘蕨菜上桌,我总要就着连扒两碗米饭。脆嫩里带着山野的清气,蒜香裹着猪油的丰腴,这是任何珍馐都无法替代的滋味。
夏日是瓜果的狂欢。外婆家门前的菜园里,竹架搭成绿色的穹顶。黄瓜悬在藤蔓间,像碧玉雕成的小月牙,表皮还缀着晶莹的露珠。随手摘一根,“咔嚓”咬下,凉丝丝的果肉在齿间碎裂,清甜的汁水顺着嘴角流淌。若是蘸上白糖,那滋味更是妙不可言,白糖的颗粒感尚未完全融化,与黄瓜的脆嫩交织成奇妙的二重奏。
荔枝红透的时节,整座山都弥漫着甜香。我们钻进荔枝林,选两棵粗壮的老树系上橡皮筋。女孩子们唱着童谣跳跃,辫子在阳光下划出金色的弧线。跳累了,就瘫在树荫下纳凉。待汗珠被山风吻干,淘气的男孩子像猴子般蹿上树梢。我也找棵结果最繁的树,攀坐在枝桠间。红玛瑙似的荔枝触手可及,剥开鳞斑状的外壳,莹白的果肉便露出来。轻轻一吮,甘冽的汁水瞬间唤醒所有味蕾,连指尖都沾着黏稠的蜜意。
如今站在都市的超市里,面对来自天南地北的果蔬,我总会想起那个漫山遍野寻找美味的童年。那些沾染着泥土清香的野果,那些需要耐心等待的佳酿,它们不只是食物,更是一个孩子认识世界的方式。我们在采摘中学会等待,在烹饪中感受温暖,在分享中体会情意。
外公离开后的那个秋天,我回到老屋。后山的野捻子依然年年结果,菜园里的黄瓜依旧挂满竹架,只是灶台前少了那个忙碌的身影。我学着舅妈的样子炒了一盘蕨菜,却总觉得少了什么味道……或许缺的不是技艺,而是那段永远回不去的时光。
味觉是刻在骨子里的乡愁。每当在异乡的深夜醒来,舌尖总会泛起米酒的甘醇、山捻子的蜜意、爆炒蕨菜的镬气。这些味道编织成无形的绳索,一头系着我漂泊的脚步,一头拴在客家山村的炊烟里。原来,童年从未远去,它只是化作了千般滋味,在我们与故乡渐行渐远的路上,亮成永不熄灭的灯火。






 粤公网安备 44150202000069号
粤公网安备 4415020200006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