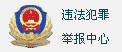○风满楼
家山马古兰
在马古兰,丘东平的家。
穿堂的风,随我开锁、推门进入这座清时“上三下三”的门厅,我听到,风掠过凹门斗檐下乌石制的门框、门槛,还有关刀状的出拱。风,抛下阳光独照在天井铺地的乌石板上,旧构其实没有改变,从前的往事心事在阳光下显影,粉刷过的窗棂脱落,露出原来灰沙的细节。
披鹤发的母亲,倚门企盼,盼来的是,儿子谭月的故人。聂绀弩的一首七律,以文字捕捉了这一刻,用文字为母亲的望儿归画了像。天井的乌石板随阳光,迈过门坎,探进厢房,发亮的包浆,刻录着东平的时光。我不忍踩下,怕留下影像的划痕。
傍村而过,为尘土荒草掩盖的惠潮古道上,童年、少年、青年的东平走过,青年、中年的我走过,足印部分重叠,我在时间的这一头。时间的那一头,马蹄声远。
风,随我转身锁门关门停滞,留下一段往事。
故园东山
速生桉终于不前,断续之间,竹、樟、鸭脚木以清晰的分辨率出现。起落的石径,链接了百年前的时光,一把锋利的钩镰,重启了钟敬文的故园东山。
垒石之上,夯土残留,一副老朽的三间过旧厝痕迹,在石径高处停顿。山楂、红柿、杜梨、柚子、柑橘,石径深处的伯公小庙,钟老少年时的诗声,还有我多年前的记忆,在高大的古荔身后隐匿。人声一时溢满园居的遗址,填补了日常的苍凉,我的到来,只是钩沉一些岁月的碎片。
薇甘菊以菊的香气,掩盖绞杀的意图,正在树间伺伏,我分明嗅到了它传递的信息。我听到了荔枝、龙眼的喘息、叹息,在我身后响起。钩镰断开的路径,悄悄愈合,揭开的幕,枝芽萌发,在脚步走远之后缓慢闭幕。
兰窗小记
鸟不经意间泊来的马樱丹,流瀑般掩饰了瓦片陷落的尴尬与狼藉,填补了天空的留白。兰窗还在,黑漆漆的一方木横棂,深邃与我对视。只须把一篮吊兰挂上,似乎故事便可复原。
我设想悄无声息潜入这钟老故地,翻越坍塌的矮墙,落地惹了碎瓦发出的断裂声,引出一流窜的猫,一声凄厉的叫声,还是打破这处废居的平静。厝与天井的边际已模糊,在杂乱中,只有一方露头的旗杆夹,提示着斯文的存在。窗外的天井,遍地瓦砾,坍塌的墙还原成了土,我须以跳跃的代价,方能换取眼前这一幕。
上三间下三间间断一天井,前后与杂货街鱼街吻合,实、虚、实间的布局如“离”卦,钟敬文青年出走之后再也没有回来。如一枚搁在海滩上洞穿无数孔的螺壳,螺、蟹先后寄居其间,惟独留下躯壳,以残缺慢慢抵御时光的侵蚀。而我,刚发好就着这午后的阳光,目睹这样一个消逝的片段。
马思聪的长巷
东向的门楼转折,三间三进连同西侧的附厝,速写般勾勒马家祖居的宏大叙事,这只是一角。鸟屎落下榕,冲天而出,盘根错节间取代后座东厢的屋宇。厚重的麻石门框、立柱、出屐、台阶,保留着步步高升的进深高远,可以想象的精美木雕缺席,依然一副大户人家的架构。散落横放的旗杆夹,记录着富贵的来处去处,镌刻着财富的刻度,如一把标尺,静静躺在墙的角落,风吹雨晒。前厅中厅的屏门,只遗下石柱础,卯位空洞,充满对榫合还有木构的念想。
马思聪最初的琴声,以口琴、手风琴的形式,在这里悠扬响起。以门楼转身的长巷,随四十九块乌石板铺垫、衔接,如钢琴的黑键,半音演奏,在海丰歌谣的吟唱、白字戏的清唱、朗朗的读书声、算盘拨动珠子上下的清脆声中,汇进熙熙攘攘的幼石街市声里,直到《思乡曲》响起,一曲成谶。琴声是对长巷的回馈与致敬,这长巷太长,终其后半生,马思聪再也无法返回涉足。
多年以后,我以鞋履叩响,这四十九个马思聪无数次叩响过的黑键,空巷足音,何以胜道?耳际是苍凉的四野,依山的落日飞雁。






 粤公网安备 44150202000069号
粤公网安备 4415020200006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