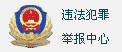○刘芝言
在汕尾,新年是从一场郑重的大扫除开始的。这种习俗有个古意的名字:“采囤”。海陆丰方言里,“采”是撷取,亦是清扫;“囤”是围积,亦是安顿。两个字合在一处,便不只是除尘,更像为将临的新岁,预先围出一方清净的天地。
关于采囤的时辰,各家略有不同。老辈人说,须在冬节前动手。冬节即冬至,此地有“食了冬节圆,就算多一岁”的老话。如此算来,清扫便是对新年最早的一声问候。也有的人家从容些,从腊月起,陆陆续续地拾掇,但总要在腊月廿四前毕其功。
少时,母亲对这时辰极为讲究。她总要请出那本纸页泛黄的老历书,指尖顺着竖排的墨字细细寻觅,择一个“宜扫舍”的吉日。若无完全合宜的,便在通行的日子里,拣个晴朗的早晨。日子定了,仪式便有了庄严的序曲。
记忆里,母亲先指挥我将杯盘吃食一一移开,覆上旧报纸。她则擎起一柄长长的竹竿,竿头牢牢系着新采的榕枝与竹叶。她仰起头,竹梢便轻轻地、绵绵地拂过天花板的每个角落,梁椽间的积尘与蛛网,便如时光的碎屑,簌簌地落进冬日的晨光里。那时的我,总觉得那竹竿长得像能触及天空。后来,竹竿换成了长柄扫帚,又换成了鸡毛掸子,唯母亲那仰首凝视的姿态,数十年如一日,未曾改变。
采囤的深意,远不止于拂去梁间的灰。它是一个家对自身彻底的检阅与更新。窗帘要卸下,浸在哗哗的水流中洗出本色;玻璃要擦到透明,仿佛不存在一般;被褥衣物经过暴晒,裹满了阳光蓬松的香气。那些蒙尘的旧物,也被请出来,在日光下接受审视:留用,或告别,完成一场静默的断舍离。这般工程浩大,常常是腰背酸软,才仅完成一半。于是剩余的琐细,便分摊到接下去的日子里,像一首长调的余韵。
于我,童年采囤中最有趣的,莫过于清理旧冰箱。老式冰箱的内壁,经年累月,结着厚厚的、象牙般的冰甲。母亲忙于洗刷蒸煮,这凿冰的活计便落在我手里。我总爱偷偷掰下一块,握在掌心,那刺骨的凉意与滑溜的触感,像握住了一个小小的、坚硬的冬天。玩着,化着,大半个上午就奢侈地溜走了。
当一切尘埃落定,家中便迎来一种前所未有的、明亮的宁静。桌椅泛着温润的光,空气里浮动着清水与阳光混合的、洁净的芬芳。老人踱步巡视,满意地颔首:“厝内清气,福气正会来。”原来,我们采囤,囤积的并非仅是洁净,更是为那浩瀚的、不可名状的“福气”,预备下一处处清晰而安稳的落点。
时代疾行,此俗却未曾褪色,只是添了从容。如今我家采囤,多不拘泥于特定吉日,拣个闲适的周末便可动手。工具愈发趁手,流程也化繁为简,但那份让家焕然一新的诚心,始终未改。
我忽然明白了,采囤并非仅仅为了驱逐旧的尘灰,而是以一种近乎虔敬的劳作,为我们那颗总在追逐与漂泊的心,预先备下一个清明、安稳的坐标。当第一缕属于新年的炊烟,从这被擦亮的灶台升起,它所奔赴的,已不是一个茫然的远方,而是一条轻轻托举着的、温暖的归途。






 粤公网安备 44150202000069号
粤公网安备 4415020200006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