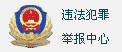○闻立
或许,是因为太多了吧,那里的山都无名无姓。它们一座挨着一座,从院子的矮墙外就开始,波浪似的向天边铺排开去,既不崎崛,也不高大,只是忠实地占据着视野的每一寸空缺。所以,人们从不费心给它们起什么名字,你喊什么,它们都答应。不像那些载入典籍、立了碑铭的名山,它们没有被赋予“迎客”或“望夫”的使命,只是以石与土的姿态,安静地存在着。
童年的许多个午后,我都是在与那些无名山的对望中度过的。祖父是个寡言的人,他的语言似乎都储存在烟斗明灭的星火里了。但他乐意带我去山脚下转悠。他不指认什么,只说:“你看。”具体要看什么,不知道。于是,我便看阳光如何从一座山的肩头,缓慢地踱到另一座山的脊背,变幻的光影给群山披上一件又一件流动的的蓑衣。看不知名的鸟,从身后的绿荫里“扑棱”一声射出,像一粒石子,稳稳落进对面山谷茂密的竹林里,只留下一串清亮的啼鸣,在沟壑间来回碰撞,渐渐碎成透明的寂静。
我最喜欢的游戏,是喊山。孩子总是淘气的,耐不住长久的沉默。我会突然把双手放在嘴边,摆成喇叭的形状,朝着最苍茫的一带山影,用尽全身力气,长长地喊一声:“哎——嗬——嗬——”
声音飞出去,清晰而尖锐。很快,它撞上了第一道山壁。但是它没有消失,它被挡住了,折返了,再送回来时,已变了些腔调,浑厚了些,圆润了些,成了“嗬——嗬——嗬——”。这还没完,折返的声音又触到侧旁的山壁,于是又一次转折,回荡,叠加上新的回响。一时间,山谷醒了。我那一声孤单的呼喊,被山们耐心地一次次接力,变腔,竟衍生出一片喧腾的和鸣。它不再是我的声音,而是成了山自己的语言。
这时,祖父脸上会浮起一抹淡淡的笑意。他磕一磕烟斗,说:“山答应了。”
是的,答应了。它们用这层层叠叠的回响,答应了一个孩子莽撞的呼喊。它们没有回应一个具体的字句,却给了你整个山谷的共鸣。你喊“你好吗”,它回应以风过松涛的“哗——”;你无意义地欢叫,它回应以鸟雀惊飞的“扑喇喇”;你静默,它便以含着溪声与虫鸣的沉默将你包裹。你的每一种表达,仿佛都能在那里找到形状相似的回声。这回声,不分尊卑,不辨雅俗,只要我喊,它就应。
长大后,我去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有名有姓的山。它们有的巍峨,有的灵秀,有的镌刻着无数题咏与传说。我仰望着它们,心中充满敬慕,却无法张口向它们随意呼喊,我想,它们也不会对我热情地应答吧。它们的美是高贵的,需要仰视,需要远观。而我家乡的那些山,是可以走进去的。它们的全部意义,似乎就在于“存在”与“回应”本身。
许多年后的一个黄昏,我独自站在异乡高楼的窗前。市声如潮水在脚下翻涌,霓虹开始咬破都市灰蓝的夜幕,一种无所依凭的孤寂突然攫住了我。那种孤寂,在鼎沸人声中反而愈发清晰,让你很想说话,但无人应答。我张了张嘴,想喊些什么,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就在那一刻,耳边毫无征兆地轰然响彻一片遥远的“哎——嗬——嗬——”“嗬——嗬——嗬——”,那是我童年的一声呼喊,是群山跨越时间与山河,递来的、从未迟到的应答。
顷刻间,我泪流满面。
原来,那些山从未沉默。它们只是把回应我的每一个音符,都妥善收藏起来了,当我在这人世走得久了,感到倦了,喉咙喑哑了,它们便在我生命的空谷里,替我响起那一片永不消散的和鸣。






 粤公网安备 44150202000069号
粤公网安备 4415020200006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