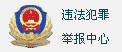○林友侨
除夕,农历一年的最后一天。不管这一天是腊月二十九还是三十,家乡海陆丰一带都叫它“三十夜”。小时候,平日早出晚归的父亲,这一天不再下地,从早到晚,都在为过年忙碌。早上,父兄齐动手,杀鸡又宰鸭。鸡是自家养的,鸭则要去圩镇换购。再加上头两天抽干村前大池塘所获淡水鱼,每家每户大概可以分得十几二十斤,这个年就过得相当丰盛了。
鸡鸭杀好后,内脏洗净切好倒进滚烫的粥里,再撒上一把蒜苗,一锅香喷喷的好粥就成了。除夕中午吃粥,既吃得好,又吃不饱,留着一个肚子,年夜饭时正好敞开怀吃。这是我家过年的前奏,村里其他人家大抵如此。下午,父亲用箩筐叠好整只煮熟的鸡,整条炊熟的鱼,整片熬熟的猪肉,配上腐竹、鸡蛋、鸡血等物什,另加三大碗装得尖如山峰的米饭,挑到祖屋“拜老公”祭拜祖先。
敬过祖先,我们吹着口哨蹦蹦跳跳回家,烧热水,挨个洗澡,换上刚做好的新衣衫,一个个像新郎新娘,变了个模样。由于兄弟姐妹多,有时家里实在困难,没法做到一人做一套新衣服,就每人做一件,缺衫的做衫,少裤的缝裤,明年再做另一件。
除夕下午三点多钟,暖暖的太阳还高高挂在天边,过年最温馨的时刻到了,翘首盼了一年的年夜饭即将开席。年夜饭俗称“围炉”,要一家人全部上桌,围坐一起,才能举筷开饭。围坐也有讲究,家中辈分最高的要坐主位,然后依次而坐。爷爷早逝,由奶奶坐大位,父亲坐在她身边侍候着。平日总在厨房忙碌的母亲,这时终于放下手中活,上桌吃饭。奶奶嫁给我爷爷后育有三子,晚年在三个儿子家轮着“食伙头”,年夜饭却必须一餐吃三家。她先在我家吃,吃个半饱,再去两个叔叔家接着吃。奶奶不到,叔叔家是不能开饭的,所以烧菜、开饭的时间要安排好,不然上桌的菜就凉了。堂弟堂妹们也只能闻着满屋、满村的鱼肉飘香干着急,不时跑出巷子来张望一下。百善孝为先,风俗千年传。村人一代又一代,都记着前人的教诲。
吃过年夜饭,太阳还舍不得下山,大大的脸盘红通通的,像喝醉了酒。我们趁着天未黑,高高兴兴跑出去玩耍。放眼眺望,冬天的田野空旷寂寥,呼啦啦的北风无处歇脚,天地间透着一股子难以形容的“冷”。此时此刻,只有家是温暖的,只有村巷是热闹的。
“年三十守夜,年初一守舍。”过年的高潮,在年三十跨入年初一的午夜,类似现在城里跨年晚会的倒计时。儿时乡村的跨年,以鸣放鞭炮为号。此时夜深人静,寒风长啸,村巷里已难觅人踪,所有人都守在自己的家里,静待吉时到来。忽然,“噼啪”的一声如平地惊雷,划破了夜的宁静,一串鞭炮在村中的某一家率先炸响,紧接着噼里啪啦、啪啦噼里,全村家家户户争先恐后点放鞭炮。古老的村庄,瞬间被轰隆炮声和滚滚浓烟淹没。
我们兄弟姐妹守在大厅,看着父亲左手拿一联炮,右手执一支香,点燃后迅疾拉开厚厚的木门,将已经噼啪响的炮竹抛向空中,降落天井或巷子里去。这叫打“开门炮”,须从门内响到门外,所以外人听到的鞭炮声,先沉闷,后响亮。开门炮一定要选得好,打得响,炸得干净,以预示新的一年红红火火、顺顺利利、丁财两旺。如果扔出去的鞭炮不响,或响了一半哑了,那是很晦气的事。鞭炮声过,村里的男孩子三五成群,手持木棍,挨家挨门翻找有无未打响的鞭炮。捡到了,或当场点燃,“嘭”的一响,引来一阵欢笑;或留到白天,插在烂泥、牛粪上,“啪”的一声,一片狼藉。那时全村哪家宽裕,鞭炮打得多,响得彻底,哪家寒碜,鞭炮买得少,臭炮多,捡炮的孩童最有发言权。无忧无虑的年龄还不懂得贫穷的无奈。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捡完炮,可以回家安心睡了。一觉醒来,春风入怀,春天到了,新的一年开始了。






 粤公网安备 44150202000069号
粤公网安备 4415020200006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