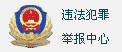○谢正义
“阳和起蛰,品物皆春。”这八个字静静地躺在泛黄的古籍里,不知过了多少寒暑。每逢立春,我总会想起它。古人仰观天象,俯察物候,将太阳黄经达315度之时,定为立春。
此日,北斗星的斗柄悄然指向寅位,正是正月建寅。在官方的历书与农人的心里,一个新的循环,自此开始。“立”,是建立,是开端;“春”,是温暖,是生发。天地在此刻,签下一份无言的契约。
中国幅员辽阔,这份契约的履行,从南到北,次第展开,从容不迫。
岭南的冬意本就浅淡。春未至,路旁的木棉已举起一树火红骨朵,沉甸甸的,像攒足了整个冬天的力气。春是轰然降临的,携着潮湿温润的空气,仿佛一夜之间,就能染绿连绵山野。
及至江南,春的脚步便缓了下来,添了几分文人般的踌躇与婉约。残冬的寒意仍在桥下水波与深深巷弄间流连,但若细看,湖畔垂柳已抽出米粒大小的芽苞,茸茸的,远望只是一抹似有还无的鹅黄。梅花正盛,清冷的幽香里,已掺进泥土苏醒的气息。雨是最寻常的,不再是冬日的冷雨,成了“沾衣欲湿”的杏花雨,淅淅沥沥,将天地笼在一片温柔的迷蒙里,仿佛万物都在为登场悄然匀妆。
春信继续北传,脚步愈发显得迟重。华北平原上,土地依然封冻,坚硬板结。风吹在脸上,仍有不容分说的力道。但若在午后向阳的墙根下静立片刻,便能察觉风里藏着一丝极细微的软和。这“软”,便是希望的先遣。天空的色调也在变,从冬日那旷远而青灰的蓝,渐渐转为柔和与明澈。最先感知这变化的,往往是鸟儿。麻雀的叫声清脆了些,聚在尚未返青的枝头,喧闹不停,像是在奔走相告什么紧要的消息。
待到关外、塞上,春则更像一个遥远的诺言。放眼望去,白雪依旧覆盖原野,山峦的线条在寒气中显得格外冷硬。但侧耳细听,冰封的河床之下,已有潺潺流水沉闷的响声;抬眼细看,向阳山坡的积雪边缘,开始变得晶莹、滑腻,缓缓塌陷,渗出亮晶晶的水线。这里的春,不是“来”的,是一寸一寸从冬天手中“挣”出来的,带着一股倔强而不屈的劲儿。
人在这样的时节交替中,心境也各有不同。
南国的人们,或许已换上轻薄的春衫,筹划着郊游踏青,他们的喜悦是外放的,与明丽的光景浑然一体。水乡的人们,或许在某个微雨的清晨,推窗望见河岸边那一片朦胧的新绿,心里蓦地生出一种淡淡的、无由的愁绪,或是宁谧的欣然。这愁与欣,皆是春的滋味。
北方的人们,感受或许更为真切而庄重。老人们会翻看皇历,念叨着“春打六九头”,将收拾了一冬的农具取出,擦拭、修整。那动作缓慢而郑重,仿佛在举行一项古老的仪式。主妇们开始拆洗厚重的冬衣被褥,在尚且清冽的阳光下,一竿一竿地晾晒出去,空气中便弥漫开阳光与棉布洁净的气息。年轻人呢,或许在某个风已不刺骨的傍晚,忽然不愿径直回家,愿意在街上多走一走,看看天色,看看行道树,心里有什么东西在微微鼓胀,痒痒的,说不分明,大抵便是“蠢蠢欲动”了。
这冬去春来,年复一年。看得久了,便也能瞧出一些道理。
冬的凛冽与枯寂,并非终结,而是一种沉潜,一种收缩与凝聚。天地将光华敛藏于根柢,正是为了此刻的勃发。没有那般彻底的封藏,便难有这般痛快的苏生。人生的况味,亦复如是。顺境如春,酣畅淋漓;逆境似冬,万籁俱寂。但只要我们心中还记着“立春”这个节气,便存下了一份笃定的盼头。知道冰终会消融,草终会返青,知道在似乎无尽的严寒之后,总有一个确凿的时点,天地会履行它的契约,将温暖与生机,重新交付人间。
这或许便是“阳和起蛰,品物皆春”的真意。它不单是自然律令的描摹,更是一份深植于我们血脉之中的、关于希望的信念。冬,是必定要去的;春,是终究要来的。在这去与来之间,我们活着,感受着,等待着,也在这无声而伟大的天地运行里,寻得了自己生命安顿的节律。






 粤公网安备 44150202000069号
粤公网安备 4415020200006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