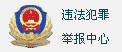○王柱森
古贝壳堤
海螺吹响号角,渤海祭出怒涛旌旗,金盔银甲跳上浪峰,虾兵蟹将举起青铜剑和铁戟,豕奔。桨橹纵横,天罗地网,征衣层层叠叠,盖不住受伤的乌贼白骨。
贝壳用年轮记载功名,全部涌上滩头。有多少破碎的贝壳,就有多少疲惫的生命从那些沙尘上重复登陆;有多少沙尘,就有多少奔赴在途中破碎。
波浪一直向前,而渤海东退六千年,退几十里,就留下一道贝壳堤,就有了地上和地下六道贝堤。古贝壳堤,无以计数的沙子,尸骨碎片也是时光。我看到一个个披着青纹外衣,吐着红舌的生灵,一批一批扑在渔人的衣冠冢上。
这里是海洋牧场,也是海洋性灵的墓地,曾经的沧海留下沟沟坎坎,还是被四季的风平息。麦地和盐田平坦,泛着碱度、硬度、盐度、温度,隆起的一道古贝堤像一条疤痕。离我最近的,是长堤上的天妃庙;埋在地下的,是我风湿的筋骨,还有遗失的珍珠。
如今,渤海还将退到哪里?即使再退去百箭地,也不会再出现贝壳堤。千万年,到底谁征服了谁?或许只有自己。再好的视线,也看不到渤海的退。可她确实一退再退。渤海是要让天空看一看,这一抱咸水的内心?
在巨鲸一样的时光机里,早晨出海,晚上有可能粉碎,但碎不掉那些蜃气长成的酸枣棵子。穿梭机一样的鸟儿,在棘刺中和妈祖的目光里,自由飞行。时光掩埋了时光,是为了重见时光,后浪赶着前浪,后面还有波浪。曾经有那么几次,决堤的海,又都退回了深处。
海水从来不会忘记涨潮,渤海渔家的孩子,还在出海。
冬天里青青的旱碱麦
旱碱麦是有方位的,属于渤海东退留下的一个叫大浪白的地方。
那里方圆几十里磨出的面粉像浪花一样白,一样的劲道。面团里,有月亮、太阳、海水一样的牵绊。
盛大的秋风收割之后,土地瘠薄。旱碱麦埋头,在寒露中铺陈,用一片片的青涩迎接冰冷和飘零,渴望,不久后的一场天下大白。
像一群走过冬天的人,春日里,扬起年轻的手臂,汇成绿波起伏;盛夏,献出金色头颅和锋芒。
脱去风尘,或被研磨成粉,或留作良种,交给土地和时令,送走煊赫的秋收,走进冬天静静生发。
注:旱碱麦是渤海湾西岸特有的小麦品种,适宜在干旱、盐碱度高的土地上生长。
一粒原盐在那里等候
好多年没吃到原盐了。天天吃盐的人,真正见过长芦原盐的不多。原盐并没有消失,就在那个生长芦草的地方。
认识它,要到长条的产床上闻闻,听听高挑结实的芦苇上长长的白毛风,晒晒膨胀的太阳。在柴火大锅炖熬的海鱼身上,在旱碱麦做成的面花里,我辨认出原盐的味道。
原盐还在渤海湾西岸的盐池里。要用泥地,用日头的刀子,用刮板揉搓才能长大,粘着泥土的色香;还要披一些风沙,在原汁原味海水特制的卤水里,经过长风的点拨,长出浑身棱角粗粝,仿佛流尽了血。
人间总是让它们粉身碎骨,让土里长大的它们重塑真身,却还是大海的基因。也有的被消解、重构,加入了其他元素,被包装。
我的眼前,跳跃着千童的羊角髻,还有那些瓮棺里未成年的盐色骸骨。其实,人们一直做着煮海为盐的活计,一直有人在武帝台登高望远。
渤海望着燕山落泪,退了又退,盐碱地里的冬小麦长了又长,一道道古贝壳堤就是海盐变色的尸体,只有黄河一直在流,曾经在这里入海,注入660年的甘甜。
大口河是禹迹九河的子孙,这条逆河一直张着大嘴呼喊:这里,就是原乡。原盐在这里守候,一粒原盐化作一滴海水,回溯着黄河的九曲、太行的巍峨。






 粤公网安备 44150202000069号
粤公网安备 4415020200006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