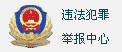○原散羊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皇泯开始在诗中不断地精神返乡。月塘墈、人和巷、将军庙、红豆树等等,都开始在诗人回忆的晨昏线上闪动生命的耀斑。那些难以言说的内在经验和灵性直观,已然成为诗人“逼仄的人生哲学”。
看过裴建平写的《冯明德的诗和远方》,了解到皇泯是一个一直在出发的人。但在这几章散文诗里,诗人却像是刚穿上鞋的孩子,一个从未走出人和巷的赤子,尽管他的“脚印是在小巷走大的”。所以什么才是生命的历练呢?难道是诗人一再提及的无所谓道路的“脚印”,“变成游泳的鱼”的脚印,还是被“种植一棵有毒的红豆树”的过去的脚印。当一个人站在时间的另一端,不断地告诫自己“不可丢失的自己”,要“战胜了自己”,他到底失去了什么呢?我问在人和巷茶馆品茶的诗人,他说“话题被喝得见底了。时间被喝得过点了”。他在一首诗中说“我的小路,弯曲后,再也拉不直”,又在另一首诗中告诉我“一条扭曲的小巷被喝直”。
这让我想起勒内·夏尔写梦的一段话:“当我达到人的状态时,我看到,在生与死之间的隔墙上,一架梯子在升起,在变大,越来越凸显。”我仿佛看到诗人皇泯把自己所有走过的脚印捡起来,装进到一个叫做散文诗的行囊中,全然不顾“诗在话语的空间相互追逐”(法国诗人让·贝罗尔),然后趁着月色回到人和巷的巷口,等夹在麻石缝里的秘密发出召唤的声音。






 粤公网安备 44150202000069号
粤公网安备 44150202000069号